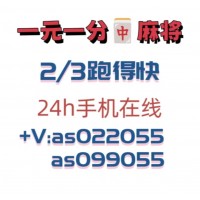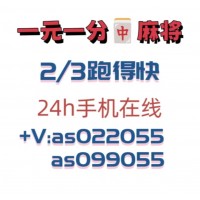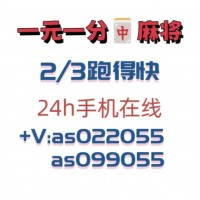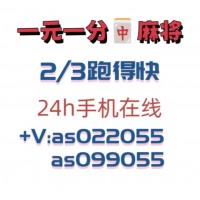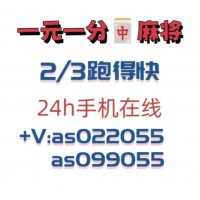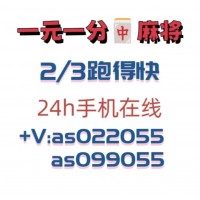/>卖凉粉的老人 缺月疏桐 每天上下班,都会看到那对卖凉粉的老两口。 我不喜欢吃凉粉,所以很少去光顾那里,但偶尔不想做饭了,也会在下班的时候坐在那里,解决一顿饭。那对老两口的热情和谦恭总是让人心里暖暖的,似乎回到了外婆身边。 有时候带着孩子去,那个老婆婆总是会给孩子另外抓一碗,不放辣子,端到孩子跟前,说:“吃吧,乖。”满眼的怜惜疼爱,仿佛是看着她最疼爱的小孙子。 我们教孩子说一声:“谢谢奶奶!”她的脸便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连声说:“不谢不谢……看你们的孩子,教育得多好!小嘴嘴多心疼啊,这城里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收钱的时候,她坚决不要孩子的那份,说:“多么一点点东西啊,看你们客气的……” 这每每让我们很不好意思,已经习惯了处处都要收钱的城市生活,面对了这样的情况,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硬赛给他们吧,觉得不合适,似乎有点拂了人家的善意;就那样顺水推舟地接受吧,心里又不是太坦然--我知道他们的生计是多么艰辛,多么不易,那可真正是辛苦啊! 摆这个小小的凉粉摊,每天起早贪黑是不用说了,光是从早到晚守着摊子,就够两老人受得呢。看他们的年纪,估计怎么都六十多岁了吧--至少比我的父母要年长一些。满脸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风霜,头发也已白了大半了,动作已经有些迟缓了,说话时带有很明显的山丹口音。我常常会想,都说落叶归根,他们这么老了怎么会到异乡的马路上摆摊呢? 老人的凉粉味道很好,再加上处在小区门口,小区住户多,所以生意也还可以,摊上总是有很多人。每当路过时,看老婆婆忙着给人抓粉,我就会为他们高兴。偶尔遇上没有人的时候,两位老人就默默地坐在凳子上,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还有一丝难以觉察的落寂和忧伤。我就在那样的落寞和疲惫中感受到了生活对于他们的压力。 有时候下班路过时会刚好碰上他们收摊,看他们将所有的东西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吃力地一个人拉,一个人推着走,我就想到“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一类的词,鼻子里总是酸酸的,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生活,对于这两个老人,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生计忙碌操劳?他们有儿女吗?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一直支撑着这样的生活? 后来,偶尔会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在帮他们收摊,我就猜想,那可能是他们的儿子吧。只是,那儿子看上去也不是能为父母撑起一片天的模样,神情中似乎有一些事不关己的漠然,我就猜想他们也可能是一家三口都靠着这个小小的凉粉摊过生活吧。不过,有个儿子也好。至少,老人的心里会有希望,会有安慰。 每每路过,看着那对老人和他们的凉粉摊,我都会这样作想,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无端地对这对老人心有牵挂,也许,是老人那落寞又疲惫的神情打动了我吧。 一天下班回来,很远就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在人行道上走着,手里举着块布,舞动着手臂,使劲甩着,嘴里还大声喊叫着,似乎是在骂人,又好像在喊口号,路边的人都远远地躲开了去。 “是个神经病,经常犯病呢。”身边的同事告诉我。 走近了才看清楚,原来那个疯子,就是那对老人的儿子! 我一下子呆住了。 好久好久,心里都很难过。 好久好久,心里都是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再看到那对老人和他们的小摊,我的心里都会生出丝丝疼痛。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从中原赶来已好多天的商人早早起来到单于城边上的交易市场开始交易,将从中原带来的大批珍珠、丝绸、茶叶换取牛羊、食盐、鹿茸、冬虫草。几年时间,单于城名声大振,匈奴的日益扩张,对汉王朝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木匠的家在小桥边上,门前一条小河,草很长,水在草底流着,不大。把家建在那儿,木匠真是聪明极了,不管怎么,总有点家乡的味道吧。房子周围是开垦出来的一小片菜地,碧绿的菜叶浓郁郁的,包着心,或者打开。有些菜,我们虽然在菜市场上见过,买过,也吃过,却不知道是怎么长出来的。 “三号铆钉”是个老光棍,今年怕有七十岁,是机务段的退休工人。他很少与人来往,一个人独居在破旧的平房里,来往走路时,倒也经常看到这位已开始驼背的老人。有时他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更多的时候则是见他拾掇院子里的花草儿。“三号铆钉”并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像是从南方过来的。据单位的老人说,“三号铆钉”年轻时结过二次婚,只是没留下一男半女,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但几乎所有人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 向左看的有左面包车型的士姹紫嫣红,向右看的有右面包车型的士万水千山,向前走的有前方的风凉水起,向后走的有反面的高谈阔论。
/>卖凉粉的老人 缺月疏桐 每天上下班,都会看到那对卖凉粉的老两口。 我不喜欢吃凉粉,所以很少去光顾那里,但偶尔不想做饭了,也会在下班的时候坐在那里,解决一顿饭。那对老两口的热情和谦恭总是让人心里暖暖的,似乎回到了外婆身边。 有时候带着孩子去,那个老婆婆总是会给孩子另外抓一碗,不放辣子,端到孩子跟前,说:“吃吧,乖。”满眼的怜惜疼爱,仿佛是看着她最疼爱的小孙子。 我们教孩子说一声:“谢谢奶奶!”她的脸便笑成了一朵盛开的菊花,连声说:“不谢不谢……看你们的孩子,教育得多好!小嘴嘴多心疼啊,这城里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收钱的时候,她坚决不要孩子的那份,说:“多么一点点东西啊,看你们客气的……” 这每每让我们很不好意思,已经习惯了处处都要收钱的城市生活,面对了这样的情况,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硬赛给他们吧,觉得不合适,似乎有点拂了人家的善意;就那样顺水推舟地接受吧,心里又不是太坦然--我知道他们的生计是多么艰辛,多么不易,那可真正是辛苦啊! 摆这个小小的凉粉摊,每天起早贪黑是不用说了,光是从早到晚守着摊子,就够两老人受得呢。看他们的年纪,估计怎么都六十多岁了吧--至少比我的父母要年长一些。满脸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风霜,头发也已白了大半了,动作已经有些迟缓了,说话时带有很明显的山丹口音。我常常会想,都说落叶归根,他们这么老了怎么会到异乡的马路上摆摊呢? 老人的凉粉味道很好,再加上处在小区门口,小区住户多,所以生意也还可以,摊上总是有很多人。每当路过时,看老婆婆忙着给人抓粉,我就会为他们高兴。偶尔遇上没有人的时候,两位老人就默默地坐在凳子上,脸上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还有一丝难以觉察的落寂和忧伤。我就在那样的落寞和疲惫中感受到了生活对于他们的压力。 有时候下班路过时会刚好碰上他们收摊,看他们将所有的东西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吃力地一个人拉,一个人推着走,我就想到“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一类的词,鼻子里总是酸酸的,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生活,对于这两个老人,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为生计忙碌操劳?他们有儿女吗?是什么力量使他们一直支撑着这样的生活? 后来,偶尔会看到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在帮他们收摊,我就猜想,那可能是他们的儿子吧。只是,那儿子看上去也不是能为父母撑起一片天的模样,神情中似乎有一些事不关己的漠然,我就猜想他们也可能是一家三口都靠着这个小小的凉粉摊过生活吧。不过,有个儿子也好。至少,老人的心里会有希望,会有安慰。 每每路过,看着那对老人和他们的凉粉摊,我都会这样作想,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无端地对这对老人心有牵挂,也许,是老人那落寞又疲惫的神情打动了我吧。 一天下班回来,很远就看见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在人行道上走着,手里举着块布,舞动着手臂,使劲甩着,嘴里还大声喊叫着,似乎是在骂人,又好像在喊口号,路边的人都远远地躲开了去。 “是个神经病,经常犯病呢。”身边的同事告诉我。 走近了才看清楚,原来那个疯子,就是那对老人的儿子! 我一下子呆住了。 好久好久,心里都很难过。 好久好久,心里都是说不出的一种滋味。 再看到那对老人和他们的小摊,我的心里都会生出丝丝疼痛。 每天太阳还没有升起,从中原赶来已好多天的商人早早起来到单于城边上的交易市场开始交易,将从中原带来的大批珍珠、丝绸、茶叶换取牛羊、食盐、鹿茸、冬虫草。几年时间,单于城名声大振,匈奴的日益扩张,对汉王朝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木匠的家在小桥边上,门前一条小河,草很长,水在草底流着,不大。把家建在那儿,木匠真是聪明极了,不管怎么,总有点家乡的味道吧。房子周围是开垦出来的一小片菜地,碧绿的菜叶浓郁郁的,包着心,或者打开。有些菜,我们虽然在菜市场上见过,买过,也吃过,却不知道是怎么长出来的。 “三号铆钉”是个老光棍,今年怕有七十岁,是机务段的退休工人。他很少与人来往,一个人独居在破旧的平房里,来往走路时,倒也经常看到这位已开始驼背的老人。有时他坐在自家门口晒太阳,更多的时候则是见他拾掇院子里的花草儿。“三号铆钉”并不是本地人,听口音像是从南方过来的。据单位的老人说,“三号铆钉”年轻时结过二次婚,只是没留下一男半女,个中原因说法不一,但几乎所有人对此有着浓厚的兴趣。 向左看的有左面包车型的士姹紫嫣红,向右看的有右面包车型的士万水千山,向前走的有前方的风凉水起,向后走的有反面的高谈阔论。原文链接:http://www.jingke.org/chanpin/486464.html,转载和复制请保留此链接。
以上就是关于全新升级跑得快。红中麻将上下分群兀然全部的内容,关注我们,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以上就是关于全新升级跑得快。红中麻将上下分群兀然全部的内容,关注我们,带您了解更多相关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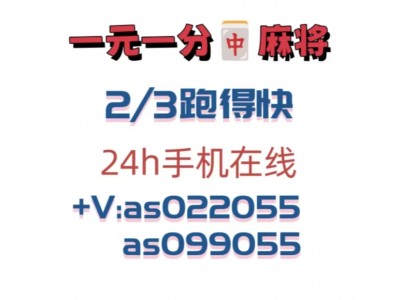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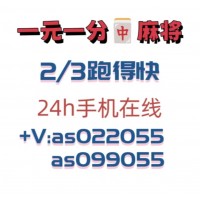


 [VIP第1年] 指数:1
[VIP第1年] 指数:1